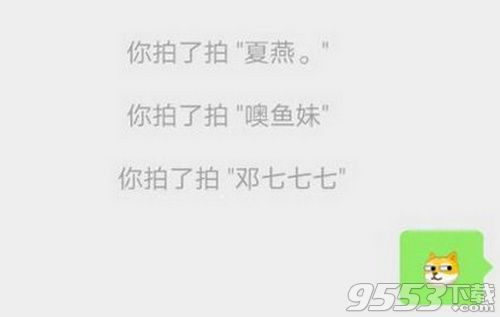专门拍部电影洗白她?真没必要
我近来越来越烦影视圈的一个热门标签——
所谓“治愈系”。
日本的影视,韩国的慢综,以及内娱借鉴这两家拍的那些玩意儿。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人嘛,无论平日里怎么挨打,回到出租屋来一集治愈剧集治愈一下就好了呀。
但……你认真这么觉得吗?
《深夜食堂》
是的,有质量、有温度的故事的确舒压解乏。
可我渐渐也察觉,不少故作温情的治愈,反而掩盖了生活的真实面。
就好比最近颇热门的一部网飞日影——
《千寻小姐》。
一句话概括剧情:一个从良的妓女用温柔救赎了一座小镇。
但我从开场皱眉到两个多钟后结束。
我不理解。
在我看来,类似“从良妓女”这样的边缘角色,是大有深度可挖的,而不该是这种干瘪虚伪的模样。
《千寻小姐》深谙“治愈”之道,开场便是一连串日系唯美剪影。
千寻(有村架纯 饰)在海边晃荡,在秋千上任风拨乱长发,在街边拥抱流浪猫。
你一打眼,嗯——她好美好善良。
善良到什么程度呢。
哪怕天天有客人到她打工的便当店性骚扰,她也能绽放花一样的笑颜。
千寻在来到海滨小镇前的职业,是援交女郎。
- 做过小姐就是不一样
跟男顾客沟通真是得心应手
- 谢谢
但她在上一份工作学到的,却尽是你能想象的最美好的品质。
例如,信任。
对每天跟踪偷拍她的小姑娘,她无条件包容。
因为她们风俗业不在乎人的身份,只在乎你的真实样貌。
又例如,仁慈。
单亲家庭里的留守儿童,她当亲生的照看。
街头被坏小孩欺负的流浪老头,她直接接回家赡养。
除此之外被千寻惠及的小镇居民还包括但不限于:原生家庭不睦的孤僻学生妹,爱看漫画的逃学宅女,双目失明的便当店老板娘,为人刻薄的妖艳单亲妈妈……
甚至是某个随机的寂寞胡子男,她也能熟稔地送上温暖……
用老本行的技能。
所以我们该怎么定义千寻?
老实讲,我不知道。
连片中被千寻视为父亲的那位“龟公”叔叔,也读不懂这个神秘女郎。
但他这评价倒是确切——
她就像个幽灵
千寻的存在最诡异的地方,就在于毫无根据。
她是凭空出现的天仙,所谓“从良”,也不过是更衬出她出淤泥而不染的标签。
一开始小镇上的人都因她这个身份议论她、排斥她。
而到最后,他们又因她的品格而发自内心地喜欢她、怀念她。
一个妓女倾倒了一座小镇,且靠的还(主要)不是色相,这题材看似很新锐深刻是吧?
但,在这份“治愈”的背后却隐藏了一个颇为老套的逻辑——
女性性善论。
简而言之,哪怕你是个妓女,曾在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,经受过最残忍的剥削和规训。
你也必须有照亮人性的真善美内核,且矢志不移。
她的女性光辉,必定要在最后如恒星般闪耀全宇宙。
可她单枪匹马对着这么大一帮老百姓做慈善,自己又图啥呢?
电影倒数一分钟终于给出了答案——
- 你之前是做什么的?
- 我在便当店打工
哦,原来她是在靠这个救赎自我,告别从前的罪孽,简称“洗白”啊。
那么,我们一直要求有更丰富的女性形象,意义又在哪里?
哪怕特别如“从良妓女”这样的设定,不也在沿着原来的逻辑被生产吗?
我实在有些不解。
描绘这样的角色最好、最生动的例子,在老早之前就有过了呀。
少时读不明白,后来越来越觉出妙处的一本书,是《金瓶梅》。
此书其实是一部底层女性的本传。
在第十五回中,西门庆携成群妻妾在高楼赏灯,而楼外即是街市。
当时,他的另几房姨太太都只象征性看了一会儿花灯,就归席吃酒去了。
只有两位仍在凭栏嬉闹——
孟玉楼与潘金莲。
西门庆作为当地旺户,妻妾出身大抵是不太差的。
哪怕二房李娇儿出身低贱,因平日不受宠,性子低调忍让,也不敢做逾矩之事。
而孟玉楼和潘金莲都是受宠的主儿,便不需要自我约束。
孟是出身于猪市街、臭水巷的市井妇人,本就粗俗。
而歌伎出身的潘则直接是放浪了——
“那潘金莲一径把白绫袄袖子儿搂着,显他那遍地金掏袖儿,露出那十指春葱来,带着六个金马镫戒指儿,探着半截身子,口中嗑瓜子儿,把嗑的瓜子皮儿都吐落在人身上,和玉楼两个嘻笑不止”。
最后,正室吴月娘见场面不好看,才喊停了这二位小妾归席。
李翰祥《少女潘金莲》
特意在此引这一段,是想说明一个问题——
经历是会在人身上留下痕迹的。
在这里潘金莲已嫁入豪门三年,习惯了上流生活,可一近街市还是原形毕露。
这就解释了千寻为何显得悬浮。
说到底,正在于她没有“痕迹”。
没有那些途径泥泞便必定要沾染的泥点子。
《千寻小姐》的核心叙事是,虽然她堕落过,但她仍保留了所有社会期待的女性品质。
哪怕还有点职业病, 也总是积极的——
当过妓女,似乎还让千寻变得更纯净了。
而我为什么要对“从良妓女”这一角色如此苛刻?
因为她们其实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类形象——
一个被父权剥夺到极点的女人,想要重新掌握对自我的掌控权,却发现困难重重。
这是古往今来各种女性困境的极致演绎。
当年令秦海璐出道即获得金马、金紫荆两座影后的电影《榴莲飘飘》,就是一个疼痛的“从良”故事。
二十一岁的秦燕是一位来自东北的姑娘。
为了赚钱,她几乎跨过整个中国,来到了香港寻找生计。
但双程证仅仅给了她3个月期限,年少的她只能操起了皮肉生意,只求在最短时间赚到钱。
在这座令家乡人无比向往的南方大都市里,秦燕过的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生活。
随时准备开工,跑完一单立刻接下一单,连吃饭只能在路上扒拉两口。
最夸张的时候,她一天要接二十多客生意。
但秦燕的妓女生涯也就持续了三个月。
在签证过期后,她便带着不少的一笔积蓄回到了老家。
结了婚,做了些小生意,成了乡里交口称赞的、“在南边赚了钱”的红人。
人们不清楚她的过往,所以纷纷捧她、恭维她。
这么看,她的“从良”过程好像很顺畅对吧?
可在洗碗冻红了手时,她蓦地愣住。
当时在香港她爱干净,每接一位客人前后都要洗一次澡。
一天洗数十次,最后浑身都红肿脱皮。
此情此景恰如当时。
就,你懂吧。
这样的日子能给人带来的只有永恒的阴影,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刻叫你陷入痛苦中,难以自拔。
至于“向阳而生”之类的叙事,只是奢望。
见识过国际都会风光的秦燕,去洗头时会要求用“纯进口”的大牌洗发水,好似已经脱胎成了上等人。
可别人一问到她在南方的“生意”,她的神色便会立刻黯淡下去。
这才是“从良”的核心调式:悲剧性。
一个女性往往是非自愿地沦为消费品,且只能回头,难以回身。
恰如《喜剧之王》里想重作乖乖女的妓女柳飘飘(张柏芝 饰)——
再度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,往常故作世故的神态已经松懈下来。
但下一秒,两条腿还是下意识地夹上了面前的男人。
很夸张,很喜剧感。
但这就是一个精准的“泥点”——
试图摆脱过去的精神束缚,却发现身体已经形成了惯性。
苦难会留下长久的幻痛。
而这种不由人的处境,其实是更值得描绘与共情的。
当“治愈”在日影中泛滥到这个程度,我其实有点困惑。
因为在昭和时代,“妓女”实际上日本电影最重视的题材之一。
从黑泽明、小津安二郎、成濑巳喜男到今村昌平等大师,皆拍摄过此类题材的杰作,而沟口健二更是把这当做整个创作生涯的母题。
他的《祗园歌女》,讲的是两位拼命想守住自尊的艺伎,如何走向沉沦。
年长的美代春(木暮实千代 饰)清高,面对不爱的男人不愿就范。
年幼的荣子(若尾文子 饰)单纯,以为这份工作可以守节。
结果她们双双得罪客人,还被老鸨在业内封杀,导致生活难以为继。
讽刺的是,她们对压迫的奋力反抗,扭头便成了酒桌上的新游戏。
他们模仿荣子咬伤嫖客的情景,当作一种刺激和情趣。
美代春是荣子的老师,更待她如亲妹妹般。
她对自己的下场毫不后悔,却只担心妹妹的将来。
于是,她最终决定出卖肉体,以换得老鸨的谅解。
第二重讽刺在这里出现——
被剥削到骨头渣都不剩的她,保住了客户的巨额订单,挽回了老鸨的名望。
由此突然成了所有人的“活菩萨”。
作为妓女的她们,绝不止代表着少数边缘群体的命运。
美代春和荣子就是那个时代、乃至这个时代女性的一个缩影。
在生活里难以见到光芒,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互扶持。
最可叹的是,在姐妹动情落泪的时刻,她们也不能尽情——
小心你的头发!
是啊,没了外貌这唯一的武器,她们又如何与生活继续斗争?
电影止步于二人在风尘中摇曳的背影。
她们隐入黑暗之中。
沟口健二有个很知名的瓜:他年轻时曾爱上一位妓女,却被对方砍了一刀。
但他却在后半生将镜头对准了底层的女性,极尽描绘她们的血泪。
或许是这一刀,让他真正共情了她们的痛吧。
你被刺上一刀
才会明白女人
其实,“妓女文学”“妓女电影”,本是东亚极其独特的文化现象。
高度成熟的日本电影是如此,国内也不例外。
往早了看,有诸如《神女》《马路天使》等杰作。
张曼玉在《阮玲玉》中重演《神女》
近了看,从《霸王别姬》《胭脂扣》《海上花》到《阿飞正传》等经典,也总不缺少鲜活的妓女形象。
巩俐在《霸王别姬》中饰妓女菊仙
后来比较有影响力的,似乎就是《金陵十三钗》。
可惜的是,该片描绘的妓女形象美则美矣,但已然落了窠臼。
倪妮饰玉墨
那十二风尘女子不忍见女学生自尽,最终决心替她们送死,自投日军罗网。
是,很伟大,很感人。
但它的底层逻辑本质与《千寻小姐》并无二致,甚至更刻板——
女性在被迫走向堕落后,便需要依靠最伟光正的行为拯救他人,以获得自身的救赎。
更直白来说,洗白名额有限,姐们儿得力争道德标兵啊。
我们干脆就去做一件顶天立地的事
改一改这千古以来的骂名
问题是,她们难道不也明白吗?这骂名分明就是欲加之罪。
她们没有必要向这个世界赎罪,身不由己,罪从来不在她们。
而如今的情况是,不单“从良”标准越来越高,写实的妓女形象本身也在肉眼可见地锐减。
不得不感到可惜,贵圈又少了一类极具表现力的面孔。
应该说,每一个来自社会边缘的女性形象,都一定会有她无可替代的张力。
《阿飞正传》中刘嘉玲饰演的风尘女露露
而至于最好的“从良”剧本,我在我极欣赏的伟大导演,川岛雄三的镜头里见过。
他的作品《女人二度出生》从标题便暗示,这是一个女性觉醒的故事。
妓院头牌小圆(若尾文子 饰)向来自诩手段高明,玩弄一票男人于股掌,但在电影的最后三分钟,她突然意识到,其实自己才是被玩弄的那一个。
于是,她将干爹送的手表转赠给同去旅行的一位学生弟,毅然告别了这最后一位情人。
瞧她在火车站想查看时间却找不见手表的一瞬——
她显然兴奋于自己的重生。
但下一刻,她在空荡的站台坐下,迷茫代替了兴奋,她开始无助地四下张望。
电影在这一刻戛然而止。
如今,我们也在不断经历这样的片刻——
因为社会发展,我们得以因各种方式顿悟、觉醒、试图独立。
但未来却似乎一片雾蒙蒙,怎么也看不清方向。
我们实际上还不知道该如何“二度出生”,因为这以往也是由社会替我们定夺。
但,撞上这片迷茫时,还请勇敢地凝望它。
它是我们需要共同探索的路,也是真正的希望。
标签: